|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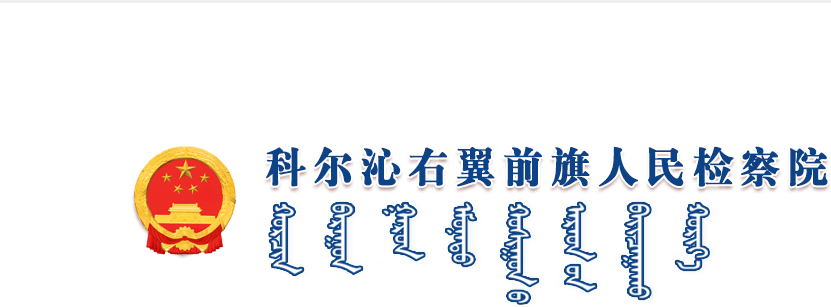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治而言,当前制度设计也面临尴尬局面。图为2018年2月11日,广东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内。视觉中国 资料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时有发生,引发公众的讨论和关切。在公众心目中,未成年人本应是祖国的花朵和社会的未来,却不时以严重犯罪实施主体的身份而见诸报端,身份角色和行为的错位引发公众的关注。如前不久发生的湖南沅江12岁男童吴某因母亲管教太严而将其刺死一事,再次挑动了公众的神经并引发广泛讨论。
当前,我国法律针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规定比较原则,缺乏刚性;因收容教养场所缺位或专门学校不足,无法满足矫治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需求,导致现在各地针对这些孩子的处遇措施基本处于空转状态。由此,公安机关在查清事实后,只能进行一定的训诫教育后放人,缺乏实质性的惩罚措施。个案发生后,媒体的大量报道及公众的密切关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当前“熊孩子”犯罪低龄化话题的热度。
公众似乎也找到了“熊孩子”犯罪低龄化的实证数据。如根据2017年6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发布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白皮书》,在该庭2009年6月至2017年6月判处的未成年罪犯234人中,犯罪年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占14.96%,且犯罪手段残忍,后果严重。
在公众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低龄未成年人事实上已具备成熟的判断能力和行为控制能力,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实施了手段残忍的犯罪就应该予以严肃惩处,而公安机关等部门依据现有法规所实施的应对举措并不能对这些孩子罚当其罪,不过是走走过场和程序。
相关教育措施的实际执行效果与不处理无异,更刺激了公众的神经。他们认为,《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应该进行修改,对这些躺在法律里边的“低龄未成年人”进行针对性的矫治。
一、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干预
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我国当前的《刑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分别进行了一定职权范围内的规定,但实际执行中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具体而言,依《刑法》规定,处刑年龄起点是14周岁;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等八项罪名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对因不满16周岁而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的时候由政府收容教养。依《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可以送专门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
但实践操作中,上述法律规定的执行却面临尴尬。劳动教养废止后,收容教养的场所和机构已经名存实亡,由此《刑法》关于收容教养的规定没有场所付诸执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然规定,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可以送专门学校进行矫治,但同时规定,对未成年人送专门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应当先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出申请,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而监护人往往考虑到专门学校产生的标签效应,不愿将已经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孩子送往专门学校。同时,专门学校近年来呈现萎缩状态,全国仅有六十余所,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贵州等地,很多地方甚至没有专门学校。
新近发生的湖南沅江男童杀母案中,因未达承担刑事责任年龄,12岁男童吴某在犯案近十天后被公安机关释放,这引发了公众对现有制度规定的强烈质疑。
惩罚措施的不到位刺激了舆论的讨论。相关部门在处理类似沅江案中“熊孩子”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尴尬:按照法律规定,虽然进行了训诫、批评教育,并对熊孩子采取了隔离单独教育等举措,但由于没有场所依靠,收容教养流于形式;家长的不同意导致专门学校教育的程序不适格而入学不能。由此,在公众看来,上述举措并不能真正惩罚犯事的“熊孩子”并给予一定的教育矫治,只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
类似重大个案发生后,制度并没有及时跟进进行修改。针对低龄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实际上没有惩罚措施的说法也就产生在公众的印象中。
二、“塔西佗陷阱”与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干预
“塔西佗陷阱”是一个西方政治学术语,说的是
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它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都会同样得罪人民”。
于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治而言,当前制度设计也面临同样的尴尬局面。
当前,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矫治制度供给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个案进行惩罚和矫治并对类案进行预防和干预方面。具体而言,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面向。
第一,严惩论。即通过修改现行《刑法》,将目前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从14周岁下调到13或者12周岁,从而将低龄未成年人的极端犯罪行为纳入《刑法》的惩治范畴,让个别极端的行为受到真正的惩罚,以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回应舆情关切。
第二,改良论。即制度的修改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由此不能有效及时应对个案的发生。在当下的制度背景下,针对低龄(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恶性犯罪,当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即根据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判断未成年人的行为责任,在不修改《刑法》前提下,特殊案件特殊处理,用“恶意”这一主观条件“补足”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这一客观限制条件,从而将《刑法》灵活适用到个案当中。
第三,完善论。即对当前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处遇机制进行完善,完善当前《刑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关规定,如:完善以教代刑的处遇制度;改变工读学校的入学程序或者完善亲职教育的程序和效果;增强法律关于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处遇制度的可操作性和衔接性,让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者能够得到有生命力的矫治和处遇举措。
综上所述,公安机关实际上已经执行了当前《刑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有关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教育矫治的规定。但未成年人需要成年人保护的主体身份与实施极端行为之间的现实错位,给了公众强烈的冲击。制度供给不足以及执行效果未能有效回应这种错位和冲击,未能满足公众对未成年人保护和社会保护的双重需要,引发了公众对当前法网是否严密以及是否有效的质疑。极端个案的不时发生更激发了公众对更加完善和强有力的教育矫治举措的需求。于是,执法部门遭遇到了“不论怎么做都会同样得罪人民”的尴尬局面。
三、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矫治制度如何精准发力
当前公众有关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矫治的讨论甚至质疑,并非一件坏事。舆论的监督和公众的质疑是健全法治的一个重要路径和手段,有助于检视当前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供给是否充足及有效,有助于倒逼相关预防和矫治机制的完善。
为有效避免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陷入“塔西佗陷阱”,我们有如下具体建言。
首先,完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矫治的法律制度供给。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频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矫治制度供给是滞后的,当前的干预手段难以有效应对低龄未成年人的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难以有效覆盖和辐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有鉴于此,需要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不完善和不合理的规定进行修改,比如修改专门学校的就学程序,理顺专门学校的入学路径与监护人的关系,从而将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顺利送入专门学校进行教育矫治。同时,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应该增设不同的教育矫治措施,增加惩罚严重不良行为的制度种类,从而为司法行政机关处理有不同罪错的未成年人提供可以选择的空间。
其次,健全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教育制度供给。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家庭教育的理念态度、方式方法、效果价值等,关系到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预防效果。问题孩子的往往产生于问题家庭。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不过是家庭教育失败的一个缩影。家庭教育制度供给的不足,严重影响到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预防效果。在新时代,为有效预防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从根本上减少或者杜绝严重不良行为的产生或者更加有针对性地教育矫治罪错未成年人,需要建立完整的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满足当前未成年人和家长的家庭教育服务诉求,针对不同层次的家庭和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更加多元专业、均衡系统、精准有效的家庭教育。
再次,建立精准多元有效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结构。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要尊遵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基本原则,不但要进行批评教育,也要建立制度化、体系化、规范化的教育矫治体系,增强和提高有罪错未成年人处遇制度供给的实践效果。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需要建立分级分类的处遇机制,不但要进行批评教育,确立警告、训诫等教育措施,也要确立和完善更加有弹性的和解、日间劳动、社区服务等具备可执行性的举措,同时要修改和完善专门学校、收容教养等举措,在完善实体处理举措的同时,增强程序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增强低龄未成年人处遇制度的实施效果和实践价值。
简言之,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处遇举措,不但要具备警示效果,让有罪错的未成年人及时认清自己行为的错误性质;更要具有问题根源意识,运用社会调查等方式明确未成年人罪错的发生机制,对症下药,建立长期的、有针对性的教育和矫治方案,以从根本上净化涉罪未成年人生活的空间和环境。